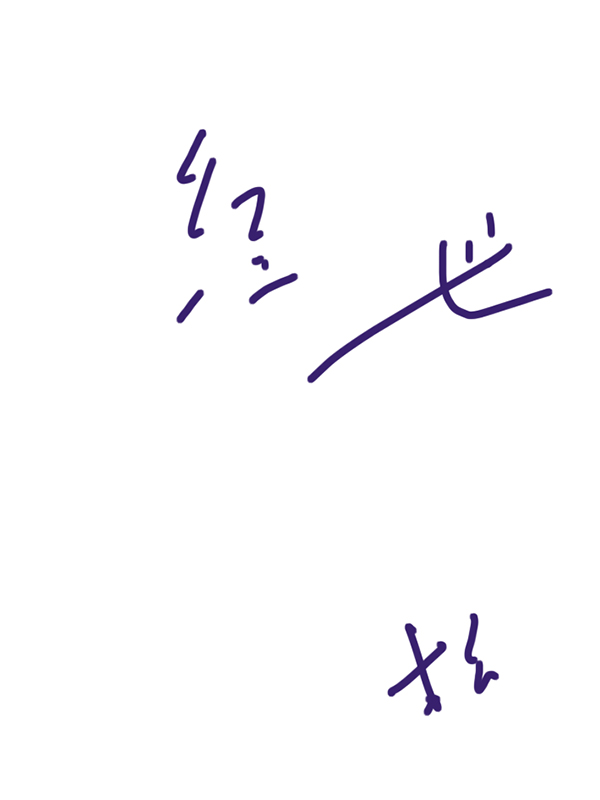牵绊
“让开,让一让——”心内的杨主任随手抓了一个路过的护士嘱咐:“去通知心内的贺医生准备手术。”
想是推床上躺了什么要紧的人,不然也不能是上了年纪的主任去跟车。
贺知书到时手术室里已经站满了人,多是各科室的主任,少有的几个年轻面孔里,还属倚着墙角站着的人最为扎眼,看起来与周围拘谨端正的一群人格格不入。
肿瘤科专治血癌的医生,他来凑什么热闹。
没由得贺知书多想,杨主任就招呼他过去:“先天性心脏病,房间隔缺损15mm,准备开胸。”
贺知书捏着止血钳守在边上,不时用镊子夹着棉球沾溢出来的血,落针可闻的手术室里猛地响起一连串仪器报警的声响。
心电图的波动骤然消失,主任撑着刀口:“心脏骤停,小贺,准备心内按摩,小苏,准备止血。”
心脏被贺知书拢在手心里一下一下轻轻按着,直到那条曲线重新出现在屏幕上,贺知书才小心地把手抽出来。
有人用镊子夹着纸巾给他擦汗,贺知书像往常一样侧头等着她擦另一边,余光扫过时就发觉了不对。
这人比之前高了太多。
艾子瑜是临时被拉来的,说是搭把手,实际上是他的主任想让他在这种情况下露个脸,多认识些人。艾子瑜不好当面拂他的好意,只好装模作样来充个数。
他看着两个护士围着主任打转,贺知书额前的汗一颗颗聚着,也不见有人去擦。
又等了片刻,艾子瑜才去柜子里取了一整套防护用具戴好,穿过人群走到贺知书身边。
缝合的过程异常顺利,艾子瑜跟着贺知书退开站在一旁等人群散去。
贺知书低头扯手上小了一号的手套,橡胶手套相互摩擦发出令人不适的声音,艾子瑜循着声音偏头看过去。
眼前人的手心里浮了一层水汽,指肚被闷久了,纵着一道道褶皱,泛着白。
贺知书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半晌,随意地搓了搓指尖,而后抬头向艾子瑜道谢:“多谢。”
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,艾子瑜就生了逗人的心思:“就一句谢,贺医生该不会现在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吧。”
他确实不知道,两人之间的交集只有每月的例会,他依稀记得这个人做过有关血癌治疗的汇报,仅此而已。
“抱歉,我……”
看他一本正经地道歉,艾子瑜自知玩笑开过了头,笑着打断贺知书的话:“逗你的,是我没说。”他敛了笑意:“艾子瑜。”
贺知书看他艰难地摸身后手术服的带子,抬手替他一条一条扯开,艾子瑜拉着手术服的领口往下扯,指着白大褂口袋上昨晚新绣上去的名字给贺知书看:“这个瑜。”
“怀瑾握瑜,和艾医生很配。”贺知书收回视线用拇指摩挲着无名指内侧的凹痕:“走吧。”
自他出生起左手无名指靠近指根的地方就带了一块胎记,浅浅的凹痕环了一圈,边缘偶尔有些不规则的痕迹,远了看像是有什么枝杈缠在上面。
左右不碍事,贺知书也就没对它格外在意,只是家里的老人曾经说过,带着胎记出生的人,往往是前世执念过重,或者牵绊过甚,他们,是来续上一辈子的缘的。
刚出门,就有人来叫贺知书去病房,他匆匆跟艾子瑜道了别,把手里的衣服递给身旁的护士:“辛苦你送去洗,我这就过去。”
主任站在病床边等他,贺知书刚站定,手里就被递了一本病例,他向病人的家属介绍:“这是我们科室最年轻有为的医生贺知书,由他负责蒋先生的后续恢复,您大可放心。”
站在病床对面的男人,约莫有五十多岁,他公事公办地冲贺知书伸出右手:“有劳。”
贺知书把病历本换了手拿着,伸手跟他的手握在一起:“应该的。”
蒋文旭迟迟不醒,贺知书被迫留下守着,他百无聊赖地翻着手上的书,是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,恰好翻到一页,上面写着:
“那一年,花开得不是最好,可是还好,我遇到你。那一年,花开得好极了,似乎专是为了你。那一年,花开得很迟,还好,有你。”
是贺知书最喜欢的一句话。
护士站的传唤铃响过一遍,第二遍刚响起来时,贺知书的手已经按在病房的门把手上了,蒋文旭听着门口的响动,松开了手里的按钮。
想是推床上躺了什么要紧的人,不然也不能是上了年纪的主任去跟车。
贺知书到时手术室里已经站满了人,多是各科室的主任,少有的几个年轻面孔里,还属倚着墙角站着的人最为扎眼,看起来与周围拘谨端正的一群人格格不入。
肿瘤科专治血癌的医生,他来凑什么热闹。
没由得贺知书多想,杨主任就招呼他过去:“先天性心脏病,房间隔缺损15mm,准备开胸。”
贺知书捏着止血钳守在边上,不时用镊子夹着棉球沾溢出来的血,落针可闻的手术室里猛地响起一连串仪器报警的声响。
心电图的波动骤然消失,主任撑着刀口:“心脏骤停,小贺,准备心内按摩,小苏,准备止血。”
心脏被贺知书拢在手心里一下一下轻轻按着,直到那条曲线重新出现在屏幕上,贺知书才小心地把手抽出来。
有人用镊子夹着纸巾给他擦汗,贺知书像往常一样侧头等着她擦另一边,余光扫过时就发觉了不对。
这人比之前高了太多。
艾子瑜是临时被拉来的,说是搭把手,实际上是他的主任想让他在这种情况下露个脸,多认识些人。艾子瑜不好当面拂他的好意,只好装模作样来充个数。
他看着两个护士围着主任打转,贺知书额前的汗一颗颗聚着,也不见有人去擦。
又等了片刻,艾子瑜才去柜子里取了一整套防护用具戴好,穿过人群走到贺知书身边。
缝合的过程异常顺利,艾子瑜跟着贺知书退开站在一旁等人群散去。
贺知书低头扯手上小了一号的手套,橡胶手套相互摩擦发出令人不适的声音,艾子瑜循着声音偏头看过去。
眼前人的手心里浮了一层水汽,指肚被闷久了,纵着一道道褶皱,泛着白。
贺知书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半晌,随意地搓了搓指尖,而后抬头向艾子瑜道谢:“多谢。”
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,艾子瑜就生了逗人的心思:“就一句谢,贺医生该不会现在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吧。”
他确实不知道,两人之间的交集只有每月的例会,他依稀记得这个人做过有关血癌治疗的汇报,仅此而已。
“抱歉,我……”
看他一本正经地道歉,艾子瑜自知玩笑开过了头,笑着打断贺知书的话:“逗你的,是我没说。”他敛了笑意:“艾子瑜。”
贺知书看他艰难地摸身后手术服的带子,抬手替他一条一条扯开,艾子瑜拉着手术服的领口往下扯,指着白大褂口袋上昨晚新绣上去的名字给贺知书看:“这个瑜。”
“怀瑾握瑜,和艾医生很配。”贺知书收回视线用拇指摩挲着无名指内侧的凹痕:“走吧。”
自他出生起左手无名指靠近指根的地方就带了一块胎记,浅浅的凹痕环了一圈,边缘偶尔有些不规则的痕迹,远了看像是有什么枝杈缠在上面。
左右不碍事,贺知书也就没对它格外在意,只是家里的老人曾经说过,带着胎记出生的人,往往是前世执念过重,或者牵绊过甚,他们,是来续上一辈子的缘的。
刚出门,就有人来叫贺知书去病房,他匆匆跟艾子瑜道了别,把手里的衣服递给身旁的护士:“辛苦你送去洗,我这就过去。”
主任站在病床边等他,贺知书刚站定,手里就被递了一本病例,他向病人的家属介绍:“这是我们科室最年轻有为的医生贺知书,由他负责蒋先生的后续恢复,您大可放心。”
站在病床对面的男人,约莫有五十多岁,他公事公办地冲贺知书伸出右手:“有劳。”
贺知书把病历本换了手拿着,伸手跟他的手握在一起:“应该的。”
蒋文旭迟迟不醒,贺知书被迫留下守着,他百无聊赖地翻着手上的书,是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,恰好翻到一页,上面写着:
“那一年,花开得不是最好,可是还好,我遇到你。那一年,花开得好极了,似乎专是为了你。那一年,花开得很迟,还好,有你。”
是贺知书最喜欢的一句话。
护士站的传唤铃响过一遍,第二遍刚响起来时,贺知书的手已经按在病房的门把手上了,蒋文旭听着门口的响动,松开了手里的按钮。